曼·雷虽然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摄影作品价值远远超越其它艺术形式的艺术家,但他能拥有一众现当代艺术大师朋友,并在现代艺术史上拥有一席之地,不仅是因为摄影技术出众,更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杰出的艺术家——达达主义奠基人。

TAG·西海美术馆《曼·雷与缪斯》展览现场,《自画像》(Self-portrait),1916/1970,丝网印刷、合成树脂玻璃
在《曼·雷与缪斯》展览起始的位置,有一件被命名为《自画像》的作品。这件作品最初于1916年12月在丹尼尔画廊展出,这件装置艺术品是曼·雷的首件“实物作品”,在之后的超现实主义者间非常流行。黑色铝制背景画下,两个按钮已失效的电铃上画着两个眼睛,艺术家印上掌印权当签名。
作品原件已经丢失或者被毀,仅留下艺术家为其拍摄的一张著名照片。1963年,他重新制作了这件作品,又于1970年将这件新作以丝网印刷的形式印制在了一块有机玻璃的背面,丝网印刷在当时被视为一种颇为前卫的艺术媒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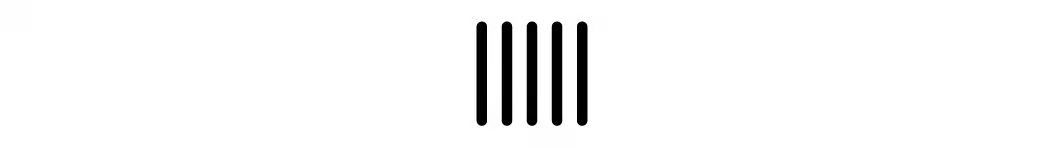

TAG·西海美术馆《曼·雷与缪斯》展览现场,现成品《美丽的香气(纽约达达杂志封面)》,曼雷&马塞尔·杜尚(罗丝·瑟拉薇),1920-1921,明胶银印(后印),36.4 × 25.4 cm
在欧洲达达主义如火如荼进行时,纽约的人们还未完全清楚达达主义意味着什么。直到1921年1月29日,《纽约电讯晨报》才发表了一篇专门论述达达主义的文章。
同年2月,曼·雷和杜尚在几家书店投放了一些达达主义的宣传材料也并未有很大反响。于是在4月份,他们共同出版了唯一一期《纽约达达主义》杂志,并得到达达主义之父特里斯唐·查拉的“官方”认可。

TAG·西海美术馆《曼·雷与缪斯》展览现场,《伊斯多尔·杜卡斯之谜》(Enigma of Isidore Ducasse ),1920 /1971,私人收藏
在TAG·西海美术馆《曼·雷与缪斯》展览中的“达达与超现实主义”版块,有一件毛毡包裹缝纫机的作品。常有观众好奇为什么没有打开包裹展示其中的物件,其实这已经是它完整呈现的状态。这件被命名为《伊斯多尔·杜卡斯之谜》的创作是为了向19世纪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Lautreamont),即伊斯多尔·杜卡斯(Isadore Ducasse)致敬。
在他一首疯狂错乱的散文诗《马尔多罗之歌》中有一精辟诗句:“就像缝纫机和雨伞在手术台上的偶遇一样美丽。”这也是超现实主义之父安德烈·布勒东所追求的,他希望通过把疯狂的生动意向表现得稀松平常来令人们感到困惑。

克里斯托与珍妮·克劳德《凯旋门的包裹 》巴黎, 2021 ,摄影:Wolfgang Volz,© 2021 Christo and Jeanne-Claude Foundation
曼·雷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件作品成为了克里斯托(Christo)“包裹”系列作品的前身。克里斯托夫妇将包裹这一概念发扬,成为了近年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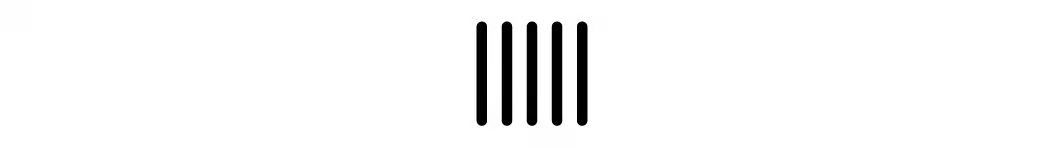
对光影的敏感以及卓越的技术让曼·雷理所应当地开始了电影拍摄。
1923年,在查拉的请求下,曼·雷为著名的“胡子心”派对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回归理性》。之后在1926年与杜尚合作完成了《贫血的电影》并独自完成了《别烦我》。1928年,曼·雷拍摄的《海星》灵感来源于罗贝尔·德诺斯所作诗歌,为了这部电影的推广,曼·雷在纽约丹尼尔画廊参加绘画与摄影展开幕式,这是他自1921年第一次回美。

《别烦我》电影截图,曼·雷,1926

TAG·西海美术馆《曼·雷与缪斯》展览现场,影片静物,源自曼·雷的电影《别烦我》,(Film still from Man Ray’s film Emak Bakia),明胶银印(原版照片),1926,23.0 × 30.0 cm ,私人收藏
1929年是曼·雷艺术电影转折的一年,十月份乌尔苏拉工作室放映了曼·雷的《骰子城堡的神秘事件》,同时放映的还有萨尔瓦多·达利与后来被誉为“超现实电影之父”的路易斯·布努埃尔拍摄的《一条安达鲁狗》。

《骰子城堡的神秘事件》影片截图,曼·雷,1929
《骰子城堡的神秘事件》也正在《曼·雷与缪斯》中展出,该短片是曼·雷在长度和叙事上的探索,也是一篇长篇游记。短片以木手掌手中的骰子开始,结尾也以相同画面结束,逐步拉开城堡全貌,记录了前往城堡上一路的风景。影片中的摇骰子、泳池抛球、玩单杠、滚地板等画面,无不体现着曼·雷贯彻在他创作中的欢乐、游嬉。
《一条安达鲁狗》宛如一场梦且极具煽动性,受到了超现实主义者的强烈赞赏与欢迎并轰动一时。与此相比,曼·雷的电影却被投入到了阴影之中。虽然曼·雷在电影方面一直未取得期望的成功,但在后人撰写艺术史时,他仍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电影的开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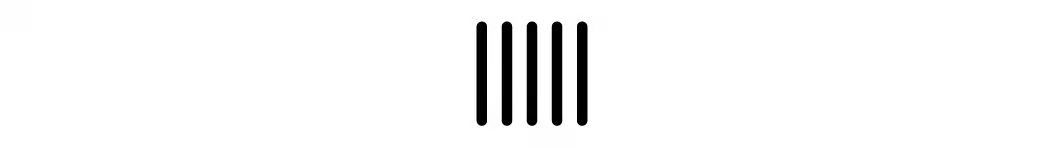
从事同一类型创作却未取得比他朋友更成功的事情不止发生在电影方面,毕竟虽然曼·雷曾说过想要成为像达·芬奇一样的人,但如达·芬奇般全能的艺术家艺史罕有,不过另一作品相较于电影就轻松很多——一系列的国际象棋。

TAG·西海美术馆《曼·雷与缪斯》展览现场,《一副国际象棋》(Chess set ),1962,9.5 × 160.0 × 57.0 cm,私人收藏
这一系列作品的闻名也与杜尚密不可分,因为杜尚本身就是一个狂热的国际象棋爱好者,棋术甚至超过了很多专业棋手,他自己也同样设计过国际象棋。
曼·雷对象棋有十分热烈的喜好,于2014年2月在台湾省高雄市立美术馆举办的题为《曼·雷——光/影/幻/境》的艺术展中就曾展出过六套曼·雷设计的西洋棋组原作。但对于曼·雷来说,下棋不止是兴趣消遣,在曼·雷眼中,黑白交错的方格矩阵除了是棋子们的战场,也像是一种对于空间的诠释方式,由此激发了他开始思考二维与三维的空间结构。
曼·雷透过最熟悉的西洋棋组开始尝试突破平面的局限。“如何在平面空间中创造最多层次的空间可能?”成为曼·雷创作生涯中持续不坠的探索重心。

TAG·西海美术馆《曼·雷与缪斯》展览现场,《绘色面包》(Pain peint ),1958/1966,透明塑料底座上的蓝色聚酯面包,27.0 × 71.0 cm,私人收藏
同样轻松戏谑的作品还有这件蓝色法棍。这是曼·雷较为晚期的雕塑作品,在这一时期曼·雷已经从纽约回到巴黎开始了相对平静的生活,此时他已经逐渐“重回绘画”,将自己的身份从摄影师——那个他早已功成名就的身份中脱离出来,而更专心于其他形式的艺术,以探索并实现他年轻时想要却未实现的更多可能。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与其说我们被称为有限的人,是因为我们从未完成任何事情,不如说我们是无限的人。”

